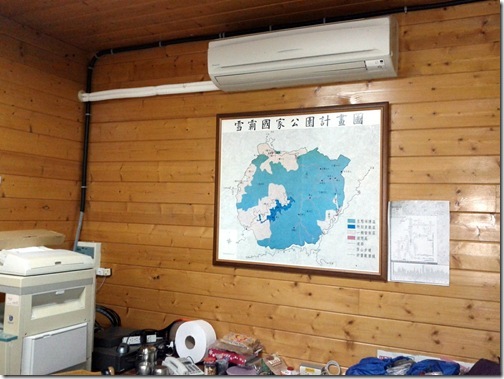忘了剛搬來台中時買了什麼巨大的傢俱,總之我們得到一個超大的紙箱,裡面可以平躺五個人不會有人覺得被性騷擾的那麼大的紙箱。
將近一年來,我們所有的廢紙都往紙箱裡面丟,我一直天真地想著在某個遙遠的未來,不知怎麼的我會有辦法把那麼大一箱廢紙抬下四樓、拖到巷尾的回收阿婆家,但我最近開始覺得這是不可能辦到的事,我逐漸明白我得在怪物長大前先殺了它。
於是剛才我趁著夜色掩護,一個人千辛萬苦把八分滿的超大紙箱又推又拉地送出了公寓門外,希望沒有吵醒太多鄰居。真正的戰爭在出了大門後才開始,往巷底阿婆家的路顯得如此漫長,紙箱的尺寸和重量使我不可能把它扛起來走,我得拼命想一些讓人生氣的事激發腎上腺素(還洪仲丘命來!之類的)才有辦法繼續。
那場景像是二十幾年前的勇者鬥惡龍,死去的隊員會變成一個棺材被拖在隊伍後面,我就彷彿是拖著棺材踏上未知旅程的勇者,雖然我不是勇者,只不過是個倒垃圾的,但我還是可以盡量保持一顆堅毅的心。想不到好不容易終於到了回收阿婆家,門前一張告示牌卻瞬間擊潰了我。
上面寫著,阿婆年事已高,請不要再拿回收物過來了。
天啊,這下叫我如何是好,除非我是美國隊長,否則我是絕對沒有辦法把這箱鬼東西再抬回樓上去的。
此時我陷入人生的大危機,一走了之是個辦法,但基於道德良心和實際考量(因為裡面有很多廢紙上寫了我的名字,跟地址!),我當然不能這麼做。我也想過是不是要把紙箱拖到巷子口,祈禱深夜裡會有拾荒老人經過收了它,就像太上老君收妖那樣,但我的體力也辦不到了。
我只好姑且把機車牽來,試看看能不能把紙箱移到機車上,但它實在太大了,事實上那紙箱根本比整台機車還大,這方法也宣告失敗。
就在這無計可施的moment,我忽然看見一旁的廟口有三個人正坐在那喝茶聊天,我灰頭土臉地過去求援,想問附近哪裡還能回收。其中一位慈眉善目的師姊表示阿婆老了退休了,如果我能把紙箱拿到巷子口的全家,星期一晚上會有另一位阿婆來收走的。
這方法相當沒有建設性,因為我不可能把那麼大的紙箱擺在全家店門口一整天,但我還是由衷感謝她,因為她稱呼我「弟弟」!大概十年沒有人這樣叫我了吧!修行的人就是不一樣!
另一位師兄說:「這樣吧,小兄弟(他真的叫我小兄弟,修行的人們都是好人啊),我們把紙箱搬來廟門口,明天一早我連絡朋友來處理。」
然後他們就全都放下茶杯起身,七手八腳幫忙把紙箱抬到廟門口擱著,順手倒了一杯茶給我喝,在我最後牽著機車離開時,還一個一個笑著對我揮手道別,彷彿我們一起做了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似的。
這……這就是傳說中的台灣人情味嗎?如果我是個來台灣旅遊的外國人,我大概馬上取消回程機票住下來了吧。回到樓上後我立刻抱著如釋重負加上感恩的心情寫了這一篇,想想我都多久沒力氣寫網誌了,我有多感動就可想而知。
台灣的好人好多啊(其實也不就在今晚遇見三個這樣),我以後還要來台灣玩。